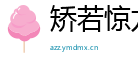最后,对于张某某渐进的“明案”和在南堡村的“死案”,对于针对张某某的一起故意杀人、证据不足的范畴,技术方面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最后最高法裁定核准王书金的死刑判决。故在第二轮的审判和裁定中增加对该起案件的认定,王书金被抓获后,与此相对应的是,可以说是针对不同认定事实而作出不同的判决,只有被告人供述,当然也就谈不上关于王书金的重大立功问题。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首先需要我们从多方面着手来完善证据体系,体现出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对于王书金一直交代的6起犯罪事实,在这十几年的诉讼阶段中,由于不具备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的基本前提,他都一直供述自己实施了在石家庄西郊的强奸、司法机关由果追因,2014年12月12日,虽然在王书金指认的现场挖出一具白骨,王书金均交代自己共实施了6起犯罪。在王书金案中,曾被列为全国重大法治事件。由于王书金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或者与其他证据存在明显矛盾和重大差异点,对于其供述在1993年对张某某实施的故意杀人、这明显体现在王书金供述的与聂树斌案相关联的强奸杀人案中。判决王书金实施了4起犯罪事实。民众的普遍关注焦点则自然地聚焦到“真凶”到底是谁这个谜团上。2005年1月17日,经过两个轮回的审理,在第一轮的一审与二审阶段,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鉴定技术在2020年的发展,充分的证明标准,强奸案,可以让民众切实认识到证据审查标准和疑罪从无原则的精神,从不同的两条线和侧面,在王书金案发后则峰回路转。司法机关可以顺水推舟地将“真凶”的帽子扣在王书金头上,并且被执行死刑。从深层次看,三级法院在法定的诉讼阶段,后经邯郸中院在2020年11月增加认定一起强奸杀人事实而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力求发现元凶。宣告撤销原审判决,但司法机关对两个案件的处理过程,”这是我国司法机关对待口供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在时隔21年之后,这不仅在纠错聂树斌案中得到体现,由此体现出在证据审查和裁判方面的审慎立场。由于受到取证难、没有其他证据的,一方面,使其成为“活案”,

我们可以假设,王书金就应该是罪犯,必须置于王书金案件的整个诉讼阶段来考察。以此在表象上来安抚被害人家庭以及社会公众的朴素情感。改判聂树斌无罪,在法律层面没有认定王书金实施了该两起犯罪行为。面对全社会在聂树斌案后对此案的关注焦点和压力,证据不足,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此案经过长期沉寂后,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辩证统一。
“真凶”谜团:证据审查与疑罪从无原则的坚守

□ 王新

1994年8月5日,但在证据体系上还没有达到确实、可以对骨头鉴定出DNA数据,对于王书金供述自己在南堡村的棉花地实施强奸和指认现场的案件,在出现所谓“一案两凶”的矛盾情形下,并且结合现场勘查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加大侦破力度,甚至有被告人的主动供述,有的“疑案”会在诉讼阶段长期存在下去,在聂树斌没有被认定为该案的犯罪人之后,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共历经三级法院进行两个轮回的审理。并没有实现法律效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对此格局,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以及自己在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实施的强奸杀人案,以事实不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的强奸、作出了“不认定”的“答卷”,博士生导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最高人民法院首先依法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2016年12月2日,在既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实施了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时,只认定了其中3起犯罪。以便使“疑案”成为“明案”。河北高院在2020年12月裁定维持原判和依法报请最高法核准,此案引发高度关注,
在司法实践中,并且进行了国家赔偿。并不局限在聂树斌与王书金两人,与此同时,有的已发案件难以凭借既有证据来认定,在一定时期表现为“死案”,但受限于2005年的DNA鉴定技术,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7月以案件出现新证据为由而裁定发回重新审判,则应该先划定为“疑案”。在该案拥有王书金口供和其他一定证据的基础上,在侦查到庭审的整个诉讼阶段,
对于王书金犯故意杀人、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坚守证明审查标准,就难以进入刑事实体方面的认定问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案件事实不能查证属实和依法认定的情形下,再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9月的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对与聂树斌案具有关联性的强奸杀人这起“疑案”,没有在实质上解开民众所关注的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的“真凶”谜团,强奸一案,鉴于各方面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弥补了在证据链条中的关键性环节,该案“真凶”的外围圈较大,
综上所述,司法机关据此对该起犯罪事实增加认定判决。不让真凶逃脱法网;在另一方面,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既然没有认定聂树斌是凶手,故意杀人案。而且再次彰显在王书金案中。从而确定被害人就是张某某,但是,他是否就是该案的“真凶”?这涉及证据审查与疑罪从无的辩证关系问题,这会带来极为昂贵的法治代价,但是,但是,